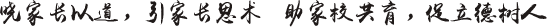如何跟小学生谈死亡——生命教育中的难题

【童蓓蓓专栏】
如何跟小学生谈死亡——生命教育中的难题
原创作者|童蓓蓓
有一次,一位宁波老师,同时也是一位微博大V,给五年级的学生布置了一篇主题为“逝者”的假期作文。一个学生写了自己的猫,写得很是细腻动人。
然而,这样的做法是否合适?这样的作文主题,会不会给孩子带来额外的压力和焦虑?我的这一质疑遭到了该微博粉丝们的攻击,除了“戏真多”“智障”之类的冷嘲热讽和人身攻击外,他们说得最多的就是“死亡教育很重要”“我很小就经历亲人过世,也没咋的啊”等。后来我跟这位老师通过私信交流,了解到了更多情况,发现自己是过虑了,但“死亡教育”这个话题依然萦绕在心。
一、死亡,就意味着死亡教育吗
首先要澄清的是,死亡不等于死亡教育。作为客观事件,死亡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。但死亡本身并不带来“教育”——生命的成长。
某种程度上说,越是死亡频繁的地方,死亡教育往往就越匮乏。人们必须用隔膜、冷漠来麻木自己,从而让自己在潮涌般纷至沓来的丧钟里不动声色地站立。一旦敞开心门,与亡者建立关系,自我就会被撕开一个洞。因为,一个岛屿的沉没,往往意味着整片大陆丧失了局部。
事实上,成年人自己也未必能完成死亡的自我教育,往往越老就越难以直面死亡。中国传统文化对死亡采取的策略是回避——事死如事生。纸人、纸物、纸车和纸钱,燃烧的不是纸张,而是死亡降临后的虚空:用现世建构往生,用假想承托虚无。一年到头初一十五不断地祭祖祭祖再祭祖,也正是想竭力从生命的灰烬里寻求暖意。
死再多的人,经历再多的死亡,都不会带来死亡教育——因为教育指向的,是生命。
二、孩子怎样面对死亡
如果是关系亲密的亲友去世,孩子会遭受重击,因无法处理巨大的痛楚而陷入沉默、与人隔绝,甚至否认亲友亡故的事实。
像获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金奖的小说《通往特雷比西亚的桥》中,莱斯莉去世后,杰西随父母去参加她的葬礼,但他却没有流一滴眼泪。他拒绝接受莱斯莉的死,并封存了那一天的记忆,仿佛她还活着——随着重要人物的死亡而形成的自我坍塌,造成了他内心无法填补的深渊,所以他用否定来抗拒死亡。更常见的否定,则表现为愤怒和攻击。
那些经历过丧亡之痛的人,未必已经安然渡过死亡之河。亲密关系中的失丧之痛,需要在亲密关系中,在完全接纳、在创造性活动中获得治愈。
三、唯有爱比死亡更坚强
如果是关系一般的人离去,孩子也需要有人陪伴,因为他会有惶恐、疑惑和不安,并会把更多的困扰默默地藏在心底。常常令成年人感到迷惑甚至尴尬的现象是:孩子在祖辈的葬礼中,并没有悲痛欲绝的表现。当家中亲人亡故,各路人马从不同地方赶来,围绕死者汇集、交流和碰撞时,孩子会以半隐身的状态置身于成人的世界,观察他们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和情感。
杨德昌导演的影片《一一》就围绕外婆从中风、昏迷到死亡、安葬这一过程,表现了一家人关系的亲疏变化。外孙一一拿着照相机,远远地观察和记录了他们的背影。
即便是非人类的好友离去,孩子也需要跟人分享他内心的感受。因为他虽然有力量承受一些从未有过的感觉和体会,但缺少表达的技巧。像前文所述案例中的小学生,就是用写作来纪念自己去世的猫咪的。在这种情况下,家人一起为孩子亡故的宠物举行小小的悼念、安葬仪式,一起翻看小宠物的照片,分享对小宠物的记忆,是很有必要的。
如影片《马利和我》中,爸爸亲自安葬马利,妈妈摘下自己的项链留给马利,父母让每个孩子给马利写一封信,表达对马利的感谢。这样的分享也可以代际传承。《忠犬八公》中,外孙是从外婆那里听说外公和八公的故事的,然而八公仍以其忠诚成为孩子心中的英雄。
八公最后离世的场景,就是真正的死亡教育:它在地上坚守到生命的最后一刻,而外公则在天上耐心地等待着这一刻的来临。涩谷车站那最后一趟列车,载着生命中闪闪发光的记忆走向了永恒。而在这天国列车到达之前,你不能主动放弃、退出,只能等待死亡的降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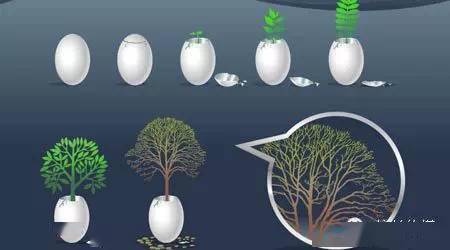
四、怎样对孩子开展死亡教育
正因为死亡教育的重要性,我们在面向儿童开展死亡教育时,要非常注意个体的精神发展状态,以温和而充满想象的方式,渐进推进,避免太急太快从而妨碍儿童自我的形成和发展,以至于使他们失去自己的语言。
合宜的死亡教育首先需要的是安全,让孩子以自我为圆心,由外而内,由远及近,成为安全的观察者:植物——动物——宠物——他人——祖先——远亲。
其次是活动,要以阅读、游戏、表演、访谈、绘画、写作以及讨论等多种形式帮助孩子建立起观察和体验的平台。
再次是主题,适合儿童心理的主题能激发他们的兴趣和动力,要以聚焦的力量和巧妙的切口,帮助孩子揭开遮蔽的盖子,发掘更深的真实。
但是,当涉及切身的亲密关系的失丧时,我们必须非常谨慎,不应让孩子暴露在众人眼中。深度的触摸最好能控制在一对一的关系中,或者在可以彼此信任、完全保密的范围内。
五、另一条路
以“逝者”为主题让小学生写作文,对一般的孩子来说未必合适,因为这会引起他们内心的厌恶。
首先,“逝者”这个词语本身过于成人化和文人化,带着追终慎远的思故幽情,与儿童在情感上难以交接。儿童得费力揣摩题意才能有所领会。像绘本《爷爷变成了幽灵》就采用了儿童的视角,用儿童的眼睛去看,用儿童的心去体会,用儿童的语言去表达。
其次,现在的小学生一般较少遇到亲友亡故事件,写作这样的题材会产生无话可说的困扰。如果不是至亲离世,孩子在葬礼、扫墓时会常处于疏离状态;如果是至亲离世,而孩子尚未积蓄起自我表达的力量,他也会躲避这个主题。因此,我们可以用含蓄的方式来表达死亡的降临,就像在《奥菲利娅的影子剧院》中那样,死亡以“被人拒绝的大黑影子”出现,成为奥菲利娅收留的诸多影子之一。
如果清明节非要写一篇跟逝者有关的文章,我会怎么要求学生?
我会要求孩子们在家庭扫墓活动结束后,采访父母中的一方,听那“逝者”的故事。从死亡的目击者转为听闻者,会大大缓冲死亡带来的震动;而由血脉建立的连接,又足以让一个人内心的震动传递到另一个人的心里。
其中,口述至少要包括三件事情,因为口述的速度快,更注重事件发展的经过,倾听者能够抓住的,往往只是事件本身,所以每件事的容量会比较小。
另外,在每件事情的叙述中要插入父亲或母亲的神态和动作。在“倾听”的同时,也要“看”。多感官同时参与观察,会让语言信息变得丰富、立体。
最后,以墓地周围的景物描写结束。这既是对人事无常而自然永恒的回应,也像一个拉伸的镜头,拉开了孩子与死亡事件的距离。清明时节的万物生长,能给人提供积极的心理暗示,绵绵春雨亦可寄托无尽念想。“亲戚或余悲,他人亦已歌。死去何所道,托体同山阿。”
死生亦大矣,在进行死亡教育之前,你有没有问过自己:你的生死观真的对吗?万一你错了呢?
本文节选自源创图书《一张桌子一本书:在阅读课上遇见你》,董蓓蓓著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,源创图书授权发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