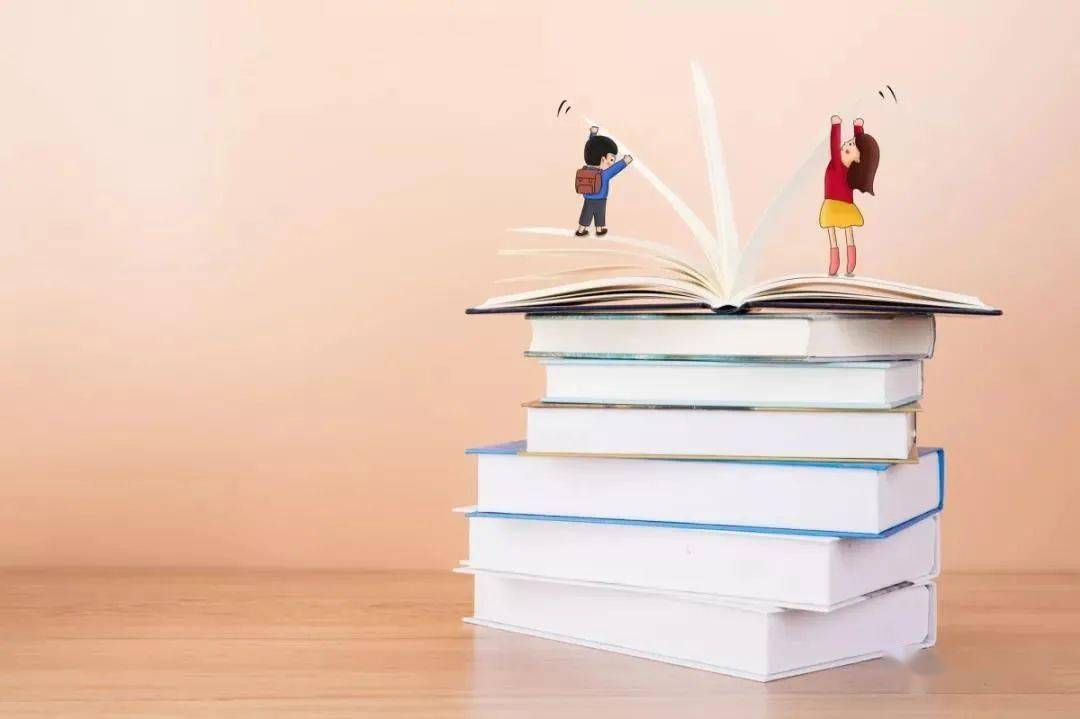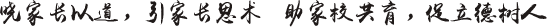杨树军: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能比问题本身更糟糕

【杨树军专栏】
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能比问题本身更糟糕
原创作者|杨树军
改革教育评价的前提,是要承认现行的评价机制与方法还不够科学,不科学的主要表现就是“唯分数、唯升学”,即应试教育依然是我们基础教育的基本问题和主要问题。
克服应试教育就是要德智体美劳“五育”并举,这是目前的社会共识。教育部最新的“意见”是:将中考体育提升到和语数外同分值水平,同时将艺术学科纳入中考总分!
在此之前,美育进中考已经在8个省份进行了试点。在智体美的问题解决之后,“德”“劳”的标准化试题也该准备了吧?
大家讨论最多的还是艺术中考。本质上,人们永远记不住自己没有“体验”过的东西,而艺术就是来体验的,标准化的艺术考试只能以知识点为主——我们在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解决了“主科”评价之后,终于要用它搞定一切了。
家长担心的是,艺术考试最终会落实为一次纸面考试,最多就考考美术鉴赏常识和乐理。这也意味着,那些普通家庭的孩子,将来光顾各种培训机构的机会增加了。
我们似乎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——患上脚气固然麻烦,但一定要截肢吗?我们可能找到了一个比问题更糟糕的解决方式。
真正的语文是诗和远方,它既无法考试,也无法评价。没有人敢说,我们民族运用母语的水平因为考试提升了——没有哪一个学科的水平是靠考试提升的。
生命因为健康而美丽——我们只有比赛,没有体育。体育带来健康更带来快乐,但当它被纳入某种评价尺度时,体育只剩了痛苦,一如我们功利而粗暴的数理化。
人有多复杂,评价就有多复杂。而当评价最终简化成一个清晰的分值时,社会能看懂了,领导有了抓手,但它没有解决任何问题——把马云和刘翔放在一起打分,这有意义吗?
德智体美劳有点像是素质教育的简化版,它可能便于操作,但也容易被教条化。当素质教育变成形式主义的时候,只能证明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打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从“多元智能”到“核心素养”,从素质教育到德智体美劳,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有没有问题?孩子一出生就是踏上了一次没有尽头的旅程,他需要的是足够的脚力与勇气,我们拼命给他的却是衣服和食物——这些东西只能迟滞他的脚步。
评价指向的一定是变化,而只有自然发生的变化才有意义……没有任何期待和面子的人生才是最美好的——这样的变化从本质上是无法精确评价的。
十九世纪后期,清政府就是最大的问题,但太平天国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吗?用应试教育的思路解决素质教育的问题——这显然是一个糟糕的解决方案。
麻风病患者会用火去炙烤自己的伤口,因为这会让他觉得“舒服”一点,尽管所有人都知道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
规定动作讲求按部就班,自选动作也有具体要求——前者是语数外这样的必考科目,后者是选考科目,选的范围也仅限于剩下那几科。
但情况就是这样,没有人对最后的结果负责,也没有人当真。我们都假装那些致命的问题不存在,反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。所有人都在一些无意义的事情上绕圈子、装模作样地忙碌着……不管怎么说,地球还在转,太阳也没那么快熄灭。
每个人都被困在了某个缝隙中,向外突破可能有危险。总共只有这么一块地,每个人都要有活干,只能你种下去后我来清理后再种……大家只是在“裤裆里面打拳”。
在这个道德感被蔑视的时代,人们的情感自动滑向了粗鄙和功利。为了自身的利益,绝大多数人只能选择“配合”……反正只是走程序,不明显违背公序良俗就行了。我们常常陷入最表面的感动中,我们无力去追问事件的意义是什么?我们不会为某种抽象的概念去牺牲自己。
可是,当我们的价值标准被剥夺的时候,我们就失去了脚下的土地……天下终将亡失——就像贪吃蛇终于咬住了自己的尾巴。
事已至此,它已经跟我们每个人有了关联——如何看待周围的世界?我们该重点关注它的哪个层面及部分?我们该如何评判世事的是非善恶?我们又该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?
教育的意义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,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它就可能比问题更坏。
崔琦1939年出生在河南平顶山宝丰县肖旗乡范庄村,他1951年赴香港投亲,因为那个特殊的年代,他此后一直未能踏上故土,直至199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。有记者曾问他是否庆幸自己当年的选择,他说:“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,我会选择留在农村,宁愿终身当个农民,家里多个干活的照顾,也许父亲就不会饿死,母亲也不会病死。”那一次他在记者面前嚎啕大哭。
我们该如何理解他的“成功”与“失败”?
教育的问题绝不限于其自身,更不是那几个硬邦邦的数字。站在无人机的角度,我们的大城市光鲜靓丽,但是,站在市民的角度,家门口是10条车道的大马路,要去马路对面都需要开车绕半天。这种光鲜跟他们有什么关系?什么跟他们有关呢?老广州的风情一半藏在她的“骑楼”里——这个多雨的南方城市首先想的是为你遮风挡雨;另外,当你晚上独自走路回家时路边咖啡馆里的人总能看到你。
十多年的寒窗经历如果不能带给我们某种自洽,再耀眼的学历有什么意义?就像大城市的繁华早已超出了我们的需求,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远得令人不适,我们仅需的那一点点温柔似乎还远在天边。屏幕上主持人和嘉宾的面部在灯光的作用下,发出越来越耀眼的白光,我们似乎已经不认同自己美丽的黄色皮肤了。同样,我们一直在鄙视的某种女性形象,在过去曾经被无限推崇——唐仕女画里浓重的五官、宽大巍峨的发髻、丰腴秾丽的身材……究竟什么是我们的传统?什么是我们应该坚守的?这一切跟我们的教育观有什么关联?
以前单位楼下有一家早餐店,在那个寡言的广东人看来牛腩汤河粉、猪杂汤米粉就是标准,你要是点个“牛腩汤米粉”,他会说牛腩配的是河粉,配米粉的是猪杂。
如果对教育的基本属性没有深刻的认识,所有的评价改革都是另一次折腾。错误的评价正在给学校制造更多的混乱,这样的问题在一个“不明白”的校长那里可能会变成一场灾难。
他们坐在主席台上原本就紧张、局促、造作,令人生厌,一开口就是权力的味道……别人不舒服、没有安全感了,他却得到了极大满足。学校的重大问题他照自己的经验和认知水平轻易敲定了,然后拿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去跟老师讨论半天。
他们喜欢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消磨时间。为了表面上的安全、为了一个壮观的场面……表面上看起来精致而复杂,就像在一个米粒上刻画了整首古诗——这毫无意义。为了“留痕”、为了推卸责任做了一堆形式,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一些谁也不能挑错的地方,准确率与做题速度成了王道;大家争相调高自己的调门儿,他们最擅长的始终是不惜代价逼学生提分。
在他们这里,教育整体上停留在野蛮时期。
那些目光坚定、沉稳有力的人呢?他们不会虚张声势,但你能感觉到一切都在掌握之中。尽管日子更难了,但他们有梦想,有责任感,在艰难的环境下不随波逐流。就算四周是漆黑的旷野,他会多点一支蜡烛,以调亮那间小木屋的光线。
作者简介:校长,已出版作品包括《子曰·我曰》《村里最好的学校》等。